難得有一晚能早睡,卻因生存壓力而失眠。
閉上眼,看到了兒時的家。那個我長大的家、後來成為了我第一個工作室的家、 進行了第一批創作,讓我走到師父身邊的家。
眼前所見,是最早期,當我開始有記憶時的模樣。
那是一個細小的單位:四百多尺,一家三口。
生活不算富裕但安穩。 簡單的生活,沒有甚麼品味但實用的裝修和家具。就像那時代所有的一切那樣簡單、樸素。
深色的釉木地板,深色木茶机上置了一台沒有遙控的電視。
兒時最深刻的一個畫面,是聽著電車「叮叮」 聲的下午,夕陽斜照進客廳。空氣中的微粒緩慢地在光影間飄盪、徐徐下降,然後在著地的一刻又飄了起來,再飄盪、再落下。記憶裡到現在也再沒看過比那更詩意的塵。
那時的我會在那裡呆呆的看著(尤其在做作業的時候)。到了今天在教攝影,才明白那是背光了的塵在深色背景前的效果。也許,在我未知甚麼是攝影、甚麼是背光的年紀,就愛上了背光拍攝的畫面。
房子一房一廳,在我出生後在廳的一邊放了「碌架床」、朱紅色金屬製,土氣和回憶也滿載。畢竟那個年代過後,這樣的床就改成了木製,金屬的、要找只有在回憶裡或照片裡。床邊放了張我已忘了是甚麼模樣的書桌。那是我最早期的房間。
記得小時上了幾堂畫畫課,就不知天高地厚的要母親坐著讓我畫素描。其實當時還未知那些畫叫素描,加上只有一支中華牌HB鉛筆的三幾歲小孩,畫不出想像中的「素描」也是正常,畫得出才真正叫人擔心這小孩日後的發展。
要是那時給我一台相機,結果也多是失敗收場。那時,沒有數碼沒有mon, 連自動暴光也未有。如無意外我不是攝影天才,而相機一定比HB鉛筆難用(現在,當然是相機比較易啦)。
廿多年後,那小孩當了個人像攝影師。不知那幅失敗了很多次、最終也沒完成的素描算不算攝影路的緣起。只知道,這長大了的人像攝影師小孩沒有幾次好好拍過他的父母,還真是說不過去。
......(待續)
後記:
這像是一編短篇小說,不過裡面的都是真人真事、我的故事。
「是甚麼人就會拍出甚麼樣的照片」似乎已繼「把握當下」和 "What's Next?" 成了葉青霖攝影班的第三口號。那麼,我那攝影眼是怎樣練成的?這點我也想知道。
「人為甚麼要生存? 人生就是一趟探索這生存意義的旅程, an eternal journey. sometimes it's painful, sometimes it's beautiful... but WORTH RIDING THROUGH...」(節錄自Yoshiki's twitter@2011-05-15)
這旅程中,攝影對你來說是甚麼?
這刻,我只知道,那回憶裡的家,會是「如果有時光機的話最想回去的地方」。
那只存在回憶裡,因我當時未懂攝影。我爸有拍照,但他的攝影眼不能代表我。至少,他大概沒詩意到要去拍下那背光的塵飛揚。
要是你看到這文章有點感動,也想起小時候的家,這就是拍照的時候。
要是看後覺得和構圖採光後製無關連張照片也沒有就覺得很無聊浪費時間,那也沒辦法,因時間已過追不回。
而且,無論大家like或dislike,這也會有下一回。
除工作外,創作從不為別人而活,這包括文字及音樂的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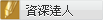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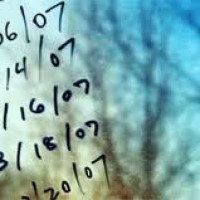
攝影裡,最美妙的事就是當你拍下照片時,照片裡的時空已不存在。
聽來很浪漫,說白了就是「把握當下」。
別說兒時的照片,我上星期備課時整理照片教材,發現自己早幾年拍下的照片其實相當幼嫩(好啦,我承認這是說好聽了的「膚淺」)。連自己也會奇怪怎麼會拍這樣的照片,還要是攝影堂的demo.......(還好這些照片都只在攝影班裡公開)
可是時間久了,不論再膚淺也是經歷,是構成現在這個自己的東西。
看著自己由膚淺變到現在無咁膚淺,不是很有趣嗎?
該做的事,沒勇氣都得做;
真正的勇氣,是不該做但喜歡做的事都去幹一把(當然不是指犯法的事),這才是勇氣。
創作上,我是那種「我喜歡就是」的人,沒理會普羅大眾是否接受得來。
提起勇氣,再多走一步,你會得到更多,享受更多。
大概大姊就是這麼的一個人了(我不喜歡稱自己為老兄 ^^")!
PS. 數碼世界,記得backup.